何乃英:結緣日本文學研究一甲子
何乃英,1935年生於北京。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曾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東方文學研究會會長。長期從事東方文學和日本文學教學、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新編簡明東方文學》、《川端康成小說藝術論》、《泰戈爾——東西融合的藝術傢》、《東方文學概論》(主編)等。
金羊網記者 朱紹傑
提及日本近代文學傢,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可能是中國讀者最為耳熟能詳的兩位。日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乃英撰寫的《夏目漱石和他的一生》《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說》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引發學界關註。
何乃英自1958年開始從事日本文學研究,至今已整整60年。他認為,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以及其他一些東方著名作傢所取得的經驗來看,其共同點是走瞭一條“東西融合”的道路,這對於當下提倡“文化自信”有著啟示意義。
對日本文學的研究以“改革開放”為界
羊城晚報:您對日本文學的興趣與研修,結緣於何種契機?
何乃英:我1958年開始在北京師范大學從事東方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從那時起就將日本文學作為教學和研究的重點之一。我對這兩位作傢比較正式的研究,是從1981—1983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生院當派遣研究員時起步的。當時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閱讀他們的作品,搜集資料,包括他們的作品全集和日本學者對他們的研究著作在內。
羊城晚報:我們國內學者對日本近代文學的研究經歷過什麼轉變?
何乃英:我國學者對日本文學研究的最大變化無疑是以改革開放為分界的。從這兩位作傢在中國的不同待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這是因為,就小說的思想內容來說,他們兩人有很大的區別:夏目漱石的前期小說主要批判日本社會的黑暗,後期小說則批判日本人內心的黑暗——自私自利。他的批判有時候還很尖銳,所以被中國人接受的時間比較早,20世紀50年代我們就翻譯出版瞭他的小說。
川端康成的小說主要追求美,既包括自然美、女性美和卑賤美,也包括虛無美和頹廢美。在某種觀點看來,有時會有一些不大健康的因素,所以被接受的時間比較晚,基本上是改革開放以後才陸續翻譯成中文出版。20世紀80年代初,還在我國學術界引起過激烈的爭論,當時主要是圍繞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國》的評價展開的。
川端康成獲諾獎讓日本文學受益
羊城晚報:夏目漱石身處西學興盛、明治維新的時代,他的作品如何處理文學藝術中傳統與現代的關系?
何乃英:夏目漱石生活在明治維新之後的時代,而且在大學讀的是英文系,又是英國留學生,所以他的文學創作受英國文學以及其他西方國傢文學的系統影響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在此之前又非常喜歡漢學,喜歡中國文化和文學。此外,作為一個日本人,他自然也深受日本民族文化和文學的影響。
以他的小說語言為例,是以日本近代生活語言為基礎,同時向日本的古典文學和曲藝學習語言,還從中國的詩歌和文章以及歐洲的文學作品中汲取養分,並將這些融化在自己的作品裡,為二葉亭四迷所開創的“言文一致”運動發揮瞭巨大的推動作用。
羊城晚報:川端康成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傢,在您看來他獲獎的原因是什麼?對於日本文學而言,諾獎有怎樣的意義?
何乃英:我以為川端康成之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他采用瞭西方人能夠接受的方法(有的是純西方的、純現代派的,有的是東西方結合的、傳統與現代結合的),較充分地表現瞭日本和日本人的美。川端康成作為日本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無疑大大地提升瞭日本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迄今為止,亞洲國傢隻有日本一國有兩位作傢獲得該項獎,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日本文學的水平,不會被人忽視。
魯迅曾贊夏目漱石“當世無與匹者”
羊城晚報: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之間的聯系是否能夠體現日本文學在近代發展中的某種聯系或傳承?
何乃英:從整體上來說,這兩位作傢的小說都產生於20世紀,夏目漱石的小說產生於1916年以前,而川端康成的小說則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初。他們都是走“東西融合”道路的。
但是由於時代不同,他們所接受的西方文學影響有所不同。在創作方法上,夏目漱石是以現實主義為主的,這種現實主義既是對日本古代寫實主義的繼承,又是對當時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傢正在流行的現實主義的吸收。
關於川端康成,從總體來看,他是主張“東西融合、以東為主”的,但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大體上說,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以前,他強調的是吸收西方文學營養,但也沒有完全忽視日本文學傳統;而在30年代中期以後,他則極力強調繼承日本文學傳統,並且越到後來越加重視日本文學傳統。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川端康成是以繼承日本文學傳統為主、以吸收西方文學營養為輔的作傢。
羊城晚報: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日本近代文學傢對於中國近代文學產生瞭怎樣的影響?
何乃英:夏目漱石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比較明顯,魯迅就是最早翻譯和介紹他作品的人之一。《魯迅全集·現代日本小說集》收入瞭漱石兩篇小品文,即《永日小品》中的《掛幅》和《克萊喀先生》。魯迅在譯著後附錄瞭“關於作者的說明”,對夏目漱石給予瞭相當高的評價。魯迅寫道:“夏目的著作以想象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作,登在俳諧雜志《子規》上的《哥兒》、《我是貓》諸篇,輕快灑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的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
不僅如此,魯迅後來回憶自己當初“怎麼做起小說來”時,也曾明確指出,夏目漱石是他那時“最愛看的作者”之一。此外,翻閱一下《魯迅日記》可以發現,魯迅直到逝世那年仍在熱心購讀當時正在陸續出版的《漱石全集》,可見他是多麼看重夏目漱石瞭。至於川端康成對於我國文學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可能是我國出現過的新感覺派文學吧。
本民族文學走向世界還需“以東為主”
羊城晚報:“文化自信”正成為文藝界的熱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文學傢為日本新文學、新文化構建所作的努力,對我們當下樹立“文化自信”有何啟示?
何乃英:我認為每個民族都應該有文化自信,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尤其應該有。但文化自信不應該是閉關自守的。如果把問題擴展開來說,這兩位作傢所走的“東西融合”的道路,可供東方其他國傢的文化和文學工作者借鑒。
例如,日本和東方許多國傢都具有悠久的古典文學歷史和豐富的古典文學遺產,但近代以來由於種種復雜的原因,文學發展的進程卻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傢,也就變成瞭“東方現代文學的底子較薄”。所謂底子較薄,主要是指東方現代文學的前身——近代文學的歷史較短,實力較弱,發展不夠充分。
羊城晚報:那麼東方現代文學怎樣才能改變這種狀況呢?
何乃英: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以及其他一些東方著名作傢所取得的經驗來看,其共同點是走“東西融合”的道路,既要繼承本民族的文學傳統,也要吸取西方文學的經驗;既要吸收西方古代和中世紀文學的經驗,也要吸收西方近代和現代文學的經驗;重點應當放在西方近代和現代文學的經驗上面。
但與此同時,隻有“以東為主”才能使東方文學具有鮮明的東方性,也就是民族性;才能使東方文學保持濃厚的東方色彩,也就是民族色彩。隻有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濃厚的民族色彩,才能使東方文學更加具有世界性,才能更加引起世界其他地區人們的重視,才能使本民族的文學更快地走向世界。這一點或許可以說是我們研究夏目漱石、川端康成所走道路的現實意義吧。
編輯:邱邱
何乃英:結緣日本文學研究一甲子金羊網2018-01-15 10:32:55
何乃英,1935年生於北京。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曾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東方文學研究會會長。長期從事東方文學和日本文學教學、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新編簡明東方文學》、《川端康成小說藝術論》、《泰戈爾——東西融合的藝術傢》、《東方文學概論》(主編)等。
金羊網記者 朱紹傑
提及日本近代文學傢,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可能是中國讀者最為耳熟能詳的兩位。日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乃英撰寫的《夏目漱石和他的一生》《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說》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引發學界關註。
何乃英自1958年開始從事日本文學研究,至今已整整60年。他認為,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以及其他一些東方著名作傢所取得的經驗來看,其共同點是走瞭一條“東西融合”的道路,這對於當下提倡“文化自信”有著啟示意義。
對日本文學的研究以“改革開放”為界
羊城晚報:您對日本文學的興趣與研修,結緣於何塑膠回收押出機|廢塑膠再生製粒機種契機?
何乃英:我1958年開始在北京師范大學從事東方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從那時起就將日本文學作為教學和研究的重點之一。我對這兩位作傢比較正式的研究,是從1981—1983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生院當派遣研究員時起步的。當時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閱讀他們的作品,搜集資料,包括他們的作品全集和日本學者對他們的研究著作在內。
羊城晚報:我們國內學者對日本近代文學的研究經歷過什麼轉變?
何乃英:我國學者對日本文學研究的最大變化無疑是以改革開放為分界的。從這兩位作傢在中國的不同待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這是因為,就小說的思想內容來說,他們兩人有很大的區別:夏目漱石的前期小說主要批判日本社會的黑暗,後期小說則批判日本人內心的黑暗——自私自利。他的批判有時候還很尖銳,所以被中國人接受的時間比較早,20世紀50年代我們就翻譯出版瞭他的小說。
川端康成的小說主要追求美,既包括自然美、女性美和卑賤美,也包括虛無美和頹廢美。在某種觀點看來,有時會有一些不大健康的因素,所以被接受的時間比較晚,基本上是改革開放以後才陸續翻譯成中文出版。20世紀80年代初,還在我國學術界引起過激烈的爭論,當時主要是圍繞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國》的評價展開的。
川端康成獲諾獎讓日本文學受益
羊城晚報:夏目漱石身處西學興盛、明治維新的時代,他的作品如何處理文學藝術中傳統與現代的關系?
何乃英:夏目漱石生活在明治維新之後的時代,而且在大學讀的是英文系,又是英國留學生,所以他的文學創作受英國文學以及其他西方國傢文學的系統影響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在此之前又非常喜歡漢學,喜歡中國文化和文學。此外,作為一個日本人,他自然也深受日本民族文化和文學的影響。
以他的小說語言為例,是以日本近代生活語言為基礎,同時向日本的古典文學和曲藝學習語言,還從中國的詩歌和文章以及歐洲的文學作品中汲取養分,並將這些融化在自己的作品裡,為二葉亭四迷所開創的“言文一致”運動發揮瞭巨大的推動作用。
羊城晚報:川端康成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傢,在您看來他獲獎的原因是什麼?對於日本文學而言,諾獎有怎樣的意義?
何乃英:我以為川端康成之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他采用瞭西方人能夠接受的方法(有的是純西方的、純現代派的,有的是東西方結合的、傳統與現代結合的),較充分地表現瞭日本和日本人的美。川端康成作為日本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無疑大大地提升瞭日本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迄今為止,亞洲國傢隻有日本一國有兩位作傢獲得該項獎,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日本文學的水平,不會被人忽視。
魯迅曾贊夏目漱石“當世無與匹者”
羊城晚報: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之間的聯系是否能夠體現日本文學在近代發展中的某種聯系或傳承?
何乃英:從整體上來說,這兩位作傢的小說都產生於20世紀,夏目漱石的小說產生於1916年以前,而川端康成的小說則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初。他們都是走“東西融合”道路的。
但是由於時代不同,他們所接受的西方文學影響有所不同。在創作方法上,夏目漱石是以現實主義為主的,這種現實主義既是對日本古代寫實主義的繼承,又是對當時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傢正在流行的現實主義的吸收。
關於川端康成,從總體來看,他是主張“東西融合、以東為主”的,但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大體上說,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以前,他強調的是廢塑膠處理濾網|處理廢塑膠垃圾濾網吸收西方文學營養,但也沒有完全忽視日本文學傳統;而在30年代中期以後,他則極力強調繼承日本文學傳統,並且越到後來越加重視日本文學傳統。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川端康成是以繼承日本文學傳統為主、以吸收西方文學營養為輔的作傢。
羊城晚報: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日本近代文學傢對於中國近代文學產生瞭怎樣的影響?
何乃英:夏目漱石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比較明顯,魯迅就是最早翻譯和介紹他作品的人之一。《魯迅全集·現代日本小說集》收入瞭漱石兩篇小品文,即《永日小品》中的《掛幅》和《克萊喀先生》。魯迅在譯著後附錄瞭“關於作者的說明”,對夏目漱石給予瞭相當高的評價。魯迅寫道:“夏目的著作以想象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作,登在俳諧雜志《子規》上的《哥兒》、《我是貓》諸篇,輕快灑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的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
不僅如此,魯迅後來回憶自己當初“怎麼做起小說來”時,也曾明確指出,夏目漱石是他那時“最愛看的作者”之一。此外,翻閱一下《魯迅日記》可以發現,魯迅直到逝世那年仍在熱心購讀當時正在陸續出版的《漱石全集》,可見他是多麼看重夏目漱石瞭。至於川端康成對於我國文學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可能是我國出現過的新感覺派文學吧。
本民族文學走向世廢塑膠加工|廢塑膠處理工廠界還需“以東為主”
羊城晚報:“文化自信”正成為文藝界的熱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文學傢為日本新文學、新文化構建所作的努力,對我們當下樹立“文化自信”有何啟示?
何乃英:我認為每個民族都應該有文化自信,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尤其應該有。但文化自信不應該是閉關自守的。如果把問題擴展開來說,這兩位作傢所走的“東西融合”的道路,可供東方其他國傢的文化和文學工作者借鑒。
例如,日本和東方許多國傢都具有悠久的古典文學歷史和豐富的古典文學遺產,但近代以來由於種種復雜的原因,文學發展的進程卻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傢,也就變成瞭“東方現代文學的底子較薄”。所謂底子較薄,主要是指東方現代文學的前身——近代文學的歷史較短,實力較弱,發展不夠充分。
羊城晚報:那麼東方現代文學怎樣才能改變這種狀況呢?
何乃英: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以及其他一些東方著名作傢所取得的經驗來看,其共同點是走“東西融合”的道路,既要繼承本民族的文學傳統,也要吸取西方文學的經驗;既要吸收西方古代和中世紀文學的經驗,也要吸收西方近代和現代文學的經驗;重點應當放在西方近代和現代文學的經驗上面。
但與此同時,隻有“以東為主”才能使東方文學具有鮮明的東方性,也就是民族性;才能使東方文學保持濃厚的東方色彩,也就是民族色彩。隻有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濃厚的民族色彩,才能使東方文學更加具有世界性,才能更加引起世界其他地區人們的重視,才能使本民族的文學更快地走向世界。這一點或許可以說是我們研究夏目漱石、川端康成所走道路的現實意義吧。
編輯:邱邱
何乃英,1935年生於北京。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曾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東方文學研究會會長。長期從事東方文學和日本文學教學、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新編簡明東方文學》、《川端康成小說藝術論》、《泰戈爾——東西融合的藝術傢》、《東方文學概論》(主編)等。
金羊網記者 朱紹傑
提及日本近代文學傢,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可能是中國讀者最為耳熟能詳的兩位。日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乃英撰寫的《夏目漱石和他的一生》《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說》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引發學界關註。
何乃英自1958年開始從事日本文學研究,至今已整整60年。他認為,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以及其他一些東方著名作傢所取得的經驗來看,其共同點是走瞭一條“東西融合”的道路,這對於當下提倡“文化自信”有著啟示意義。
對日本文學的研究以“改革開放”為界
羊城晚報:您對日本文學的興趣與研修,結緣於何種契機?
何乃英:我1958年開始在北京師范大學從事東方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從那時起就將日本文學作為教學和研究的重點之一。我對這兩位作傢比較正式的研究,是從1981—1983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生院當派遣研究員時起步的。當時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閱讀他們的作品,搜集資料,包括他們的作品全集和日本學者對他們的研究著作在內。
羊城晚報:我們國內學者對日本近代文學的研究經歷過什麼轉變?
何乃英:我國學者對日本文學研究的最大變化無疑是以改革開放為分界的。從這兩位作傢在中國的不同待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這是因為,就小說的思想內容來說,他們兩人有很大的區別:夏目漱石的前期小說主要批判日本社會的黑暗,後期小說則批判日本人內心的黑暗——自私自利。他的批判有時候還很尖銳,所以被中國人接受的時間比較早,20世紀50年代我們就翻譯出版瞭他的小說。
川端康成的小說主要追求美,既包括自然美、女性美和卑賤美,也包括虛無美和頹廢美。在某種觀點看來,有時會有一些不大健康的因素,所以被接受的時間比較晚,基本上是改革開放以後才陸續翻譯成中文出版。20世紀80年代初,還在我國學術界引起過激烈的爭論,當時主要是圍繞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國》的評價展開的。
川端康成獲諾獎讓日本文學受益
羊城晚報:夏目漱石身處西學興盛、明治維新的時代,他的作品如何處理文學藝術中傳統與現代的關系?
何乃英:夏目漱石生活在明治維新之後的時代,而且在大學讀的是英文系,又是英國留學生,所以他的文學創作受英國文學以及其他西方國傢文學的系統影響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在此之前又非常喜歡漢學,喜歡中國文化和文學。此外,作為一個日本人,他自然也深受日本民族文化和文學的影響。
以他的小說語言為例,是以日本近代生活語言為基礎,同時向日本的古典文學和曲藝學習語言,還從中國的詩歌和文章以及歐洲的文學作品中汲取養分,並將這些融化在自己的作品裡,為二葉亭四迷所開創的“言文一致”運動發揮瞭巨大的推動作用。
羊城晚報:川端康成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傢,在您看來他獲獎的原因是什麼?對於日本文學而言,諾獎有怎樣的意義?
何乃英:我以為川端康成之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他采用瞭西方人能夠接受的方法(有的是純西方的、純現代派的,有的是東西方結合的、傳統與現代結合的),較充分地表現瞭日本和日本人的美。川端康成作為日本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無疑大大地提升瞭日本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迄今為止,亞洲國傢隻有日本一國有兩位作傢獲得該項獎,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日本文學的水平,不會被人忽視。
魯迅曾贊夏目漱石“當世無與匹者”
羊城晚報: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之間的聯系是否能夠體現日本文學在近代發展中的某種聯系或傳承?
何乃英:從整體上來說,這兩位作傢的小說都產生於20世紀,夏目漱石的小說產生於1916年以前,而川端康成的小說則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初。他們都是走“東西融合”道路的。
但是由於時代不同,他們所接受的西方文學影響有所不同。在創作方法上,夏目漱石是以現實主義為主的,這種現實主義既是對日本古代寫實主義的繼承,又是對當時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傢正在流行的現實主義的吸收。
關於川端康成,從總體來看,他是主張“東西融合、以東為主”的,但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大體上說,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以前,他強調的是吸收西方文學營養,但也沒有完全忽視日本文學傳統;而在30年代中期以後,他則極力強調繼承日本文學傳統,並且越到後來越加重視日本文學傳統。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川端康成是以繼承日本文學傳統為主、以吸收西方文學營養為輔的作傢。
羊城晚報: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日本近代文學傢對於中國近代文學產生瞭怎樣的影響?
何乃英:夏目漱石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比較明顯,魯迅就是最早翻譯和介紹他作品的人之一。《魯迅全集·現代日本小說集》收入瞭漱石兩篇小品文,即《永日小品》中的《掛幅》和《克萊喀先生》。魯迅在譯著後附錄瞭“關於作者的說明”,對夏目漱石給予瞭相當高的評價。魯迅寫道:“夏目的著作以想象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作,登在俳諧雜志《子規》上的《哥兒》、《我是貓》諸篇,輕快灑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的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
不僅如此,魯迅後來回憶自己當初“怎麼做起小說來”時,也曾明確指出,夏目漱石是他那時“最愛看的作者”之一。此外,翻閱一下《魯迅日記》可以發現,魯迅直到逝世那年仍在熱心購讀當時正在陸續出版的《漱石全集》,可見他是多麼看重夏目漱石瞭。至於川端康成對於我國文學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可能是我國出現過的新感覺派文學吧。
本民族文學走向世界還需“以東為主”
羊城晚報:“文化自信”正成為文藝界的熱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文學傢為日本新文學、新文化構建所作的努力,對我們當下樹立“文化自信”有何啟示?
何乃英:我認為每個民族都應該有文化自信,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尤其應該有。但文化自信不應該是閉關自守的。如果把問題擴展開來說,這兩位作傢所走的“東西融合”的道路,可供東方其他國傢的文化和文學工作者借鑒。
例如,日本和東方許多國傢都具有悠久的古典文學歷史和豐富的古典文學遺產,但近代以來由於種種復雜的原因,文學發展的進程卻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傢,也就變成瞭“東方現代文學的底子較薄”。所謂底子較薄,主要是指東方現代文學的前身——近代文學的歷史較短,實力較弱,發展不夠充分。
羊城晚報:那麼東方現代文學怎樣才能改變這種狀況呢?
何乃英: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以及其他一些東方著名作傢所取得的經驗來看,其共同點是走“東西融合”的道路,既要繼承本民族的文學傳統,也要吸取西方文學的經驗;既要吸收西方古代和中世紀文學的經驗,也要吸收西方近代和現代文學的經驗;重點應當放在西方近代和現代文學的經驗上面。
但與此同時,隻有“以東為主”才能使東方文學具有鮮明的東方性,也就是民族性;才能使東方文學保持濃厚的東方色彩,也就是民族色彩。隻有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濃厚的民族色彩,才能使東方文學更加具有世界性,才能更加引起世界其他地區人們的重視,才能使本民族的文學更快地走向世界。這一點或許可以說是我們研究夏目漱石、川端康成所走道路的現實意義吧。
編輯:邱邱
何乃英:結緣日本文學研究一甲子金羊網2018-01-15 10:32:55
何乃英,1935年生於北京。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曾任中國外國文學學會東方文學研究會會長。長期從事東方文學和日本文學教學、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新編簡明東方文學》、《川端康成小說藝術論》、《泰戈爾——東西融合的藝術傢》、《東方文學概論》(主編)等。
金羊網記者 朱紹傑
提及日本近代文學傢,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可能是中國讀者最為耳熟能詳的兩位。日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何乃英撰寫的《夏目漱石和他的一生》《川端康成和他的小說》由華中科技大學出版社出版,引發學界關註。
何乃英自1958年開始從事日本文學研究,至今已整整60年。他認為,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以及其他一些東方著名作傢所取得的經驗來看,其共同點是走瞭一條“東西融合”的道路,這對於當下提倡“文化自信”有著啟示意義。
對日本文學的研究以“改革開放”為界
羊城晚報:您對日本文學的興趣與研修,結緣於何塑膠回收押出機|廢塑膠再生製粒機種契機?
何乃英:我1958年開始在北京師范大學從事東方文學教學和研究工作,從那時起就將日本文學作為教學和研究的重點之一。我對這兩位作傢比較正式的研究,是從1981—1983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學研究生院當派遣研究員時起步的。當時我的主要工作,就是閱讀他們的作品,搜集資料,包括他們的作品全集和日本學者對他們的研究著作在內。
羊城晚報:我們國內學者對日本近代文學的研究經歷過什麼轉變?
何乃英:我國學者對日本文學研究的最大變化無疑是以改革開放為分界的。從這兩位作傢在中國的不同待遇,就可以清楚地看出這一點。這是因為,就小說的思想內容來說,他們兩人有很大的區別:夏目漱石的前期小說主要批判日本社會的黑暗,後期小說則批判日本人內心的黑暗——自私自利。他的批判有時候還很尖銳,所以被中國人接受的時間比較早,20世紀50年代我們就翻譯出版瞭他的小說。
川端康成的小說主要追求美,既包括自然美、女性美和卑賤美,也包括虛無美和頹廢美。在某種觀點看來,有時會有一些不大健康的因素,所以被接受的時間比較晚,基本上是改革開放以後才陸續翻譯成中文出版。20世紀80年代初,還在我國學術界引起過激烈的爭論,當時主要是圍繞川端康成的代表作——《雪國》的評價展開的。
川端康成獲諾獎讓日本文學受益
羊城晚報:夏目漱石身處西學興盛、明治維新的時代,他的作品如何處理文學藝術中傳統與現代的關系?
何乃英:夏目漱石生活在明治維新之後的時代,而且在大學讀的是英文系,又是英國留學生,所以他的文學創作受英國文學以及其他西方國傢文學的系統影響是理所當然的。但是,他在此之前又非常喜歡漢學,喜歡中國文化和文學。此外,作為一個日本人,他自然也深受日本民族文化和文學的影響。
以他的小說語言為例,是以日本近代生活語言為基礎,同時向日本的古典文學和曲藝學習語言,還從中國的詩歌和文章以及歐洲的文學作品中汲取養分,並將這些融化在自己的作品裡,為二葉亭四迷所開創的“言文一致”運動發揮瞭巨大的推動作用。
羊城晚報:川端康成是首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日本作傢,在您看來他獲獎的原因是什麼?對於日本文學而言,諾獎有怎樣的意義?
何乃英:我以為川端康成之所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因為他采用瞭西方人能夠接受的方法(有的是純西方的、純現代派的,有的是東西方結合的、傳統與現代結合的),較充分地表現瞭日本和日本人的美。川端康成作為日本首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無疑大大地提升瞭日本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迄今為止,亞洲國傢隻有日本一國有兩位作傢獲得該項獎,這從一個方面反映出日本文學的水平,不會被人忽視。
魯迅曾贊夏目漱石“當世無與匹者”
羊城晚報: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之間的聯系是否能夠體現日本文學在近代發展中的某種聯系或傳承?
何乃英:從整體上來說,這兩位作傢的小說都產生於20世紀,夏目漱石的小說產生於1916年以前,而川端康成的小說則產生於20世紀70年代初。他們都是走“東西融合”道路的。
但是由於時代不同,他們所接受的西方文學影響有所不同。在創作方法上,夏目漱石是以現實主義為主的,這種現實主義既是對日本古代寫實主義的繼承,又是對當時英國和其他西方國傢正在流行的現實主義的吸收。
關於川端康成,從總體來看,他是主張“東西融合、以東為主”的,但在不同時期有所變化。大體上說,上世紀30年代中期以前,他強調的是廢塑膠處理濾網|處理廢塑膠垃圾濾網吸收西方文學營養,但也沒有完全忽視日本文學傳統;而在30年代中期以後,他則極力強調繼承日本文學傳統,並且越到後來越加重視日本文學傳統。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川端康成是以繼承日本文學傳統為主、以吸收西方文學營養為輔的作傢。
羊城晚報: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日本近代文學傢對於中國近代文學產生瞭怎樣的影響?
何乃英:夏目漱石對中國現代文學的影響比較明顯,魯迅就是最早翻譯和介紹他作品的人之一。《魯迅全集·現代日本小說集》收入瞭漱石兩篇小品文,即《永日小品》中的《掛幅》和《克萊喀先生》。魯迅在譯著後附錄瞭“關於作者的說明”,對夏目漱石給予瞭相當高的評價。魯迅寫道:“夏目的著作以想象豐富、文詞精美見稱。早年所作,登在俳諧雜志《子規》上的《哥兒》、《我是貓》諸篇,輕快灑脫,富於機智,是明治文壇上的新江戶藝術的主流,當世無與匹者。”
不僅如此,魯迅後來回憶自己當初“怎麼做起小說來”時,也曾明確指出,夏目漱石是他那時“最愛看的作者”之一。此外,翻閱一下《魯迅日記》可以發現,魯迅直到逝世那年仍在熱心購讀當時正在陸續出版的《漱石全集》,可見他是多麼看重夏目漱石瞭。至於川端康成對於我國文學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可能是我國出現過的新感覺派文學吧。
本民族文學走向世廢塑膠加工|廢塑膠處理工廠界還需“以東為主”
羊城晚報:“文化自信”正成為文藝界的熱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等文學傢為日本新文學、新文化構建所作的努力,對我們當下樹立“文化自信”有何啟示?
何乃英:我認為每個民族都應該有文化自信,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尤其應該有。但文化自信不應該是閉關自守的。如果把問題擴展開來說,這兩位作傢所走的“東西融合”的道路,可供東方其他國傢的文化和文學工作者借鑒。
例如,日本和東方許多國傢都具有悠久的古典文學歷史和豐富的古典文學遺產,但近代以來由於種種復雜的原因,文學發展的進程卻落後於西方先進國傢,也就變成瞭“東方現代文學的底子較薄”。所謂底子較薄,主要是指東方現代文學的前身——近代文學的歷史較短,實力較弱,發展不夠充分。
羊城晚報:那麼東方現代文學怎樣才能改變這種狀況呢?
何乃英:從夏目漱石、川端康成以及其他一些東方著名作傢所取得的經驗來看,其共同點是走“東西融合”的道路,既要繼承本民族的文學傳統,也要吸取西方文學的經驗;既要吸收西方古代和中世紀文學的經驗,也要吸收西方近代和現代文學的經驗;重點應當放在西方近代和現代文學的經驗上面。
但與此同時,隻有“以東為主”才能使東方文學具有鮮明的東方性,也就是民族性;才能使東方文學保持濃厚的東方色彩,也就是民族色彩。隻有具有鮮明的民族性和濃厚的民族色彩,才能使東方文學更加具有世界性,才能更加引起世界其他地區人們的重視,才能使本民族的文學更快地走向世界。這一點或許可以說是我們研究夏目漱石、川端康成所走道路的現實意義吧。
編輯:邱邱
- 廢棄物處理|廢棄物濾網處理 塑膠回收押出機|廢塑膠再生製粒機專業服務廠商
- 塑膠回收押出機|廢塑膠再生製粒機 塑膠熱融押出濾網產生廢料該找哪方面的廠商解決
- 塑膠回收押出機|廢塑膠再生製粒機 請推薦廢塑膠原料|廢塑膠原料處理專業廠商
文章標籤
全站熱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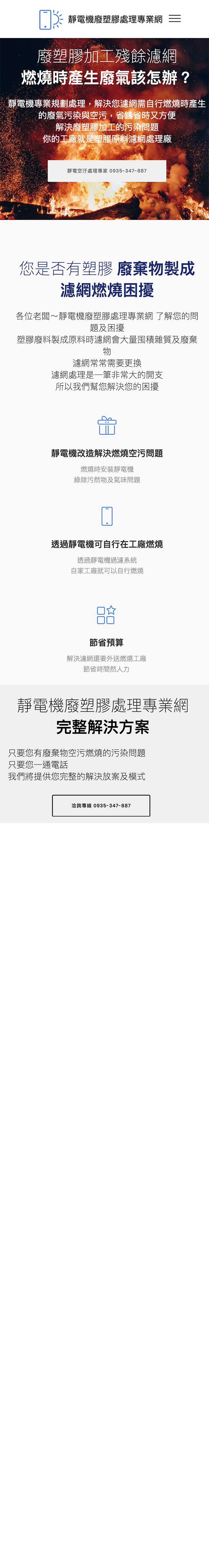


 留言列表
留言列表


